译学文献 | 历史游戏研究:作为数字史学发展新方向
翻译技术教育与研究 2024年09月09日 00:00 陕西
以下文章来源于数字人文研究 ,作者卢雅怀
数字人文领域研究热点和前沿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原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以及国内外相关机构的主要活动与成果推介;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荣誉学位教学平台以及数字人文教学的推广交流;《数字人文研究》的推广平台。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数字人文研究》2024年第2期”;参考文献格式:卢雅怀.历史游戏研究:作为数字史学发展新方向[J].数字人文研究,2024,4(2):3-21.全文PDF已在知网、万方上发表,此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历史游戏研究:作为数字史学发展新方向
卢雅怀
摘 要 历史游戏研究作为蓬勃发展的新领域,日益吸引历史学者包括数字史学学者的目光。文章探讨作为数字史学工作的历史游戏研究,梳理历史游戏研究领域的诞生与演进,总结该领域的已有共识与启示,并指出:当下的“数字史学”并非“计量史学”的直接延续,而以公众史学理想、媒介技术关怀为背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游戏研究与数字史学一脉相承。历史游戏研究探索电子游戏作为数字大众媒介,如何改变历史知识的生产、传播、接受方式与公众历史意识,构成了一窥数字时代历史学变革方向的窗口。将历史游戏研究纳入数字史学,有助于澄清数字史学的界定与范畴,也为拓展深化数字史学提供了抓手。
关键词 电子游戏; 历史游戏研究;数字史学; 媒介革命; 知识生产模式
作者简介 卢雅怀,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Email:luyahuai@pku.edu.cn。
0
引言
本文首先通过概述数字史学的诸种路径,澄清数字史学的界定与理解;接着梳理历史游戏研究的发展进路,阐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与数字史学关注息息相关,或可被视为广义的数字史学工作;最后总结历史游戏研究现有工作与展望,它们对数字史学工作的可能启示。本文尝试提出:历史游戏研究也是数字史学的一项重要探索;从数字史学的工作框架与理念出发,有助于我们理解与定位历史游戏研究的兴起与使命;历史游戏研究亦能对数字史学的拓展、深化做出贡献。

《文明》系列
1
历史游戏研究作为数字史学工作
数字技术已经深入到我们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内外学者都曾指出,就所有人都在使用数字技术而言,“当下的所有历史学家都是数字史学学家”;任何借助电脑技术、互联网技术、信息化技术等数字技术的学者,“都能理直气壮地称自己的工作属于数字史学” 。数字史学的开放性,使得它能够支持多种不同的史学工作、接纳更具挑战性的新探索。电子游戏作为当代最为重要的数字媒介,对它的研究也可被视为某种数字史学工作吗?本节将数字史学的已有工作及特征与历史游戏研究进行对比,分析历史游戏研究与数字史学的交集。
数字史学声名日显,其发展更是时代所需。与此同时,即使是学界中人,对于“什么是数字史学”依然存有困惑、观点各异:数字史学是一些研究工具、一套做历史的普遍方法,还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亦或是一种倾向或精神?即在数字史学的“定性”上,依然未有定论。数字史学作为拓新,既是实践导向乃至于实践先行的,同时又是一套理想。因此,讨论数字史学的可能性,既要关注以论文、专著形式出现的学术成果、发展畅想,更要看到那些难被学术发表体系承认的探索。
虽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一切使用数字技术创造、增进或是传播历史研究与学术成果的工作,都可以被归于数字史学 ,但在其他史学同行的理解中,数字史学主要还是意味着史料数字化工作。这种一般印象也符合实情,无论国内外,数字史学都首先专注于史料数字化、资料库与数据库建设,及数字史料永久保存等基础性工作。
这种工作现状,既体现了数字史学如何根植于史学传统之中,亦展现了数字史学当下的困境与瓶颈。作为历史遗产保存的史料数字化工作既非数字史学的全部,也不是数字史学的独一特征。梁晨与李中清指出,史料收集、整理与保存作为史学工作的根基,正是历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立足点。历史学在理解与应对新技术时,也长期以历史遗产保存为重心。从19 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历史学不断引入照片、缩微胶卷、影印等技术来提高史料的可得性与存留时长,数字化只是这一系列探索中最新的一步。就资料库与数据库的建设而言,搭建也只是第一步,要避免成为“死库”或是“信息孤岛”,它还需要建设内嵌的分析工具,保障后期的维护与更新,与其他库及平台建立交换、共享机制,向更广泛的人群开放。
因此,史料的数字化只是数字史学中“很小的一部分”,在此之外,还包括对数字化史料和数字史料的深度挖掘,以及对研究成果的呈现与传播全过程。随着历史文本数字化这一数字史学“基础建设”逐渐完善,数字史学未来发展方向也更加多元。
1.1.2 作为新“阅读”方式的数据挖掘与量化分析
由此可知,网络与多媒体技术在数字史学兴起与发展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数字史学”这一术语的诞生,可以追溯到 1997-1998 年“维吉尼亚数字史学中心”( Virginia Center for Digital History,VCDH) 的建立,中心创始人之一威廉·托马斯三世指出,他们最初使用“数字史学”一词,是为了指代和讨论“阴影谷”(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1993) 这一网络资料库项目。数字史学做出开创性共享的另一个机构是“罗伊·罗森茨威格历史与新媒体中心”( Roy Rosenzweig Center for History and New Media),它的奠基人也推出了数字史学的早期经典《数字史学:在网络上收集、保存和呈现过去》( Digital History: A Guide toGathering,Preserving,and Presenting the Past on the Web,2005)。从这些研究中心与工作导论的关键词来看,数字史学与网络技术、新媒体技术的深度关联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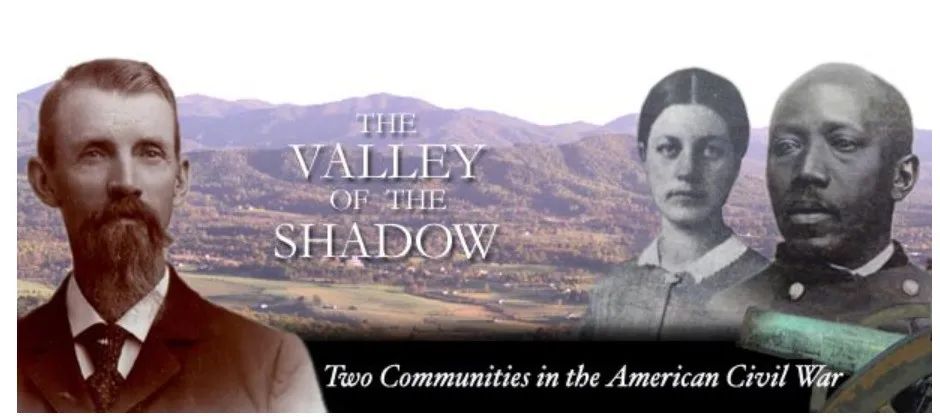
数字史学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公共史学关怀,在历史研究的数字化转型中,公共史学也持续发挥重要助推作用。首先,史料数字化,也是对于历史遗产的保存与再现,是否能与其他资料库互联、合作,有着怎样的社会开放度,是史料库建设的重要标准,其中的公共史学意义不言而喻。其次,进行大数据挖掘的重要初衷与动力之一,就是关注大众与边缘群体日常生活。历史上来看,量化历史研究的两次浪潮,都以回应社会问题和冲突,提供对人民大众“有用的“历史为目标。第三,数字史学对媒介技术的应用,则更体现数字史学与公共史学间的相互交融关系。一方面,公共史学必须跟上数字媒介的发展,才能触及更广泛的公众。另一方面,因为数字媒介天然的社会性,几乎所有的数字史学工作终将进入公众领域。
这种似乎无所不包的数字史学工作是否有其焦点或突破口?——公众关怀与对大众媒介的使用,一开始就位于数字史学的中心。赫尔本·扎格斯马(Gerben Zaagsma) 等学者更是进一步指出,媒介与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是一个能为数字史学工作赋予使命意义、提供内在统一性的切入点:印刷制品不再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唯一媒介,甚至不再是标准媒介;新的媒介技术改变了并将持续变更知识生产与传播。
那么,数字时代最独特、能触及最广泛公众的媒介是什么?电子游戏无疑榜上有名。一方面,电子游戏是对已有媒介的融合,是“融合媒介的极致”;另一方面,“游戏还未被发明”,它的边界尚未封闭,是一种可能与已有媒介截然不同, 要求打破传统的媒介理解的存在,由此构成对于知识生产与传播传统的冲击与变革。
就电子游戏对历史学的影响而言,虽然它的历史不足百年,但已经日益取代电视剧与电影,成为青少年获得历史知识的第一来源。就其与数字史学诸种路径的关联而言,电子游戏不仅以其流行程度,构成了深入公共史学工作的重要载体,就数字史学最应关注的媒介特性而言(见本文1.1.3与1.1.4),它更是非线性、交互性与参与性的最突出展现。
不仅如此,电子游戏早在“数字史学”这一术语出现与广泛使用之前,就进入了广义上的数字史学的发展历程之中。1971 年,三位美国大学生为了辅助自己在公立高中的实习工作,制作了一款名为《俄勒冈之旅》( The Oregon Trail) 的软件,1974 年,它被移植到教育计算机系统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俄勒冈之旅》风靡美国课堂,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著名的游戏化教学范例。历史学的教师们成了最早制作与启用电子游戏辅助教学的先锋,《俄勒冈之旅》不仅是历史教育游戏的代表,更成为所有游戏化教学探索中的经典。

虽然历史学的教研人员率先走向电子游戏,但整个历史学界对电子游戏议题的关注与接纳却缓慢得多。在“电子游戏研究”发展的早期阶段,我们的确鲜见历史学家的身影。要到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历史学家才开始更多投入到电子游戏作为媒介对于历史研究的机遇与挑战的研究工作之中,探讨“电子游戏作为历史”( Digital Games as History) 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在“历史游戏研究”的名义下,主要聚集的是历史学受训的学者,因为当代的技术门槛和专业化高度,他们很少能真正参与一款历史题材游戏的制作,更多的是将电子游戏作为文本、作为物件、作为媒介进行学术探讨。因此,制作历史题材电子游戏,与分析游戏中历史元素及其影响,是两个尚未紧密联合的工作领域。
随着探索推进和深入,历史游戏研究者并没有将自己的工作,局限于对所谓“历史题材游戏”进行批评,而是从类型与内容更多元的游戏中,看到电子游戏在呈现历史、传递历史信息、构成历史记忆、影响公众历史意识等方面的现状与可能性。由此,历史游戏研究开始关注电子游戏这一数字媒介及其对历史学的挑战。
不仅如此,历史游戏研究的发展本身,也体现出数字技术中的去中心化、打破知识垄断的潜能。虽然电子游戏本身在美国、日本起步更早,但发达国家并未成为数字游戏研究话语的领路人与设定者,发展中国家比如捷克的学者们无论是在“历史游戏”的制作还是历史游戏研究方面都颇受赞誉。而我国也出现了全球最早一批投身历史游戏研究工作,并在路径方法上颇具独创性与特色的学者。比如刘梦霏以游戏档案馆为载体,将保存游戏历史、促进游戏作品创作、提升游戏知识分子和游戏素养培养结合,不仅对游戏史、游戏中的历史再现进行学术研究,也关注、参与游戏改变历史的实践;曹琪以“电子游戏改造人类世界的历史”课堂为载体和渠道,在技术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复合语境下对电子游戏进行考察。没有将视野局限于电子游戏中的历史信息,而是从“电子游戏中的历史”与“有电子游戏参与的历史”这两者的互动中,看到电子游戏等数字媒介引导下的转型与变革,也构成了我国历史游戏研究者的鲜明学术特色。
由此可见,历史游戏研究与数字史学研究看似是两个领域,但如果认为数字史学的中心内容在于历史学家关注“普通人的历史”,尝试触及更大公众,为此将数字技术纳入史料收集、研究、呈现与交流工作,公众也经由数字技术参与历史知识的生成与传播之中,两方共同推动历史实践的数字化转型,那么,电子游戏作为当代最重要的数字媒介,应该落入数字史家的工作范围。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开始提出,游戏上的、想象上的探索,提供了一条“能克服数字史学与传统历史工作之间张力的路径”。历史学家日益在游戏之中,看到历史学密切与公众的联系,应对数字时代转型、以新的形式研究与呈现历史的可能性。
2
历史游戏研究的演进
除了实践先行,历史游戏研究也在公众—媒介关怀上与数字史学一脉相承。历史游戏研究者很早就意识到,电子游戏不仅是另一个新颖流行的教辅工具,还蕴含着媒介革命的潜质。它一方面挑战现有的历史权威关系,另一方面提供了呈现历史研究的新形式。历史游戏研究由此也构成了对于数字史学乃至于历史学学科领域本身的拓展与反思。
与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相较,历史学很晚才开始关注电子游戏。其中,率先做出回应的是承担基础教育工作的中学老师们。如前文提及,为辅助高中历史课堂而开发的《俄勒冈之旅》(1971 年),是教育游戏的先锋与经典。对它的理论反思则相对滞后,要到十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在教育技术类刊物的评论板块中,才开始出现对它的探讨。历史学与历史教育专刊的回应则更晚,以《历史教师》( The History Teacher) 为例:它作为历史教育学会( SHE) 会刊,是美国最广为人知与认可的历史教育专刊,然而直到2001年刊登的一篇讨论电影之教学意义的论文之中,才一笔带过“电子游戏“的情况。
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历史学对电子游戏反应滞后,问题或许不在于“游戏”而在于“电子”:历史课堂以及历史教育专刊本身并不排斥“游戏”。使用基于纸笔、卡牌或是角色扮演等方式的模拟( simulations) 游戏辅助教学,在历史课堂中早有传统;对模拟游戏的经验总结、理论研讨,也一直在历史教学研究中有着一席之地。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历史教学》就刊载文章,讨论如何将视听材料与各类模拟游戏用于历史教学。这些都说明,对于历史教学而言,比起引入活跃课堂的“游戏”,取用新的数字媒介技术是一个更大的挑战。面对技术门槛,历史教育依然是历史学中最快转向取用和分析电子游戏的领域,这源于它们的公共史学承诺,包括对历史权威的反思,对史学教育反思,对历史普及新方式的探索。
要到 2004 年,才有了以“历史教学中的电子游戏“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库尔特·斯夸尔( KurtD. Squire) 以《文明》( Civilization) 这一策略类游戏( simulation game) 的典范作为考察对象,进行教学法上的反思:传统的历史学习变成了单调的背诵记忆,疏于让学生真正体验、经历历史学家的探究工作——使用游戏或许能打破这些弊端。
斯夸尔这篇经典的博士论文,属于教育学而非历史学工作。要再过十年,到21世纪10年代的后半叶,历史学受训的教师们才会更积极地加入游戏促进、革新历史教学的讨论之中。最早的探索,比如 2007 年安德鲁·麦克迈克尔( Andrew McMichael) 同样以《文明》等策略游戏为重点考察对象,反思威权主义的历史教学方式,探索电子游戏为此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什么,并着重于实践细节,分享自己的课程设计与效果。
到了 2011 年,在中学历史课堂中使用电子游戏已经初具规模,以至于出现了专门对此提供指导的教学手册。作者杰里迈亚·麦考尔( Jeremiah McCall) 对于历史教研人员转向电子游戏的解释,很有代表性:教师们担心,以学院史家的出版物作为唯一权威的历史教育体系,很容易变为对所谓“历史事实”的灌输,进而迫使学生放弃自己的理性。而真正的历史教育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历史技艺与素养,包括搜索与评估史料,勇于形成自己对于过去的诠释,与他人的诠释进行批判性对话。此外,因为“历史本质上是选择性地呈现过去,它可以使用多种形式与媒介”,学生需学会分析除了手稿、印刷本等文字材料之外的多种媒介材料。对于21世纪的学生而言,他们还亟需培养应对数字化未来的技能。这首先就意味着要具备解读数字媒体和多媒体材料的能力,比如解读和使用电子游戏的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斯夸尔还是麦克迈克尔——将策略模拟游戏纳入历史课堂,或是后续的历史教学,虽然取用了更多类型的电子游戏,但总以反思学院史家—历史教师—历史学生关系,及思考数字时代学生理应具备的历史技艺与素质作为一以贯之的主题。由此可见,历史教研人员转向电子游戏,远不止是因为电子游戏是青少年间的流行玩意,还源于公共史学和数字史学视角的理解与信念:“做历史不是专家的特权……文本不是做历史的唯一合法途径”,即在数字时代,历史学学生需要掌握分析新类型的材料、用新媒介展现和传播历史诠释的素养。电子游戏和书写一样,也是“二手文献”,也是一种诠释形式,可以也需要得到分析、批判和评估。在这个意义上,电子游戏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与数字史家关注数据挖掘的原因类似:数字时代出现了新类型的史料,也就需要培养相应的新的分析与“阅读”技能。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出现了一些与电子游戏相关的零散的史学理论探讨。最开始,学界在术语及其界定上还缺乏共识:不确定何谓“历史”游戏,也没有对于历史学者的游戏研究工作的统称,更要慢慢摸索研究问题、方法与理论。或许正因开启新研究领域之艰难,需要参照或对比,历史学者从最开始就将电子游戏置于其他数字媒介之中,在数字技术发展与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理解电子游戏对于历史学的启发或挑战。
威廉·尤瑞奇欧( William Uricchio)2005年的《模拟、历史与电脑游戏》一文,被视为这方面的奠基之作与典范。尤瑞奇欧一方面强调电子游戏的颠覆性,认为电子游戏不同于包括影音多媒体在内的其他媒介,不仅是历史再现( representation),更是历史模拟( simulation),这使得它能够探讨反事实的历史可能性。另一方面,尤瑞奇欧将电子游戏置于更广大的历史范式变更之中,认为游戏实际上在实践后结构主义等对媒介的关注、对编史学的挑战。
尤瑞奇欧的经典作品充分展现了对电子游戏进行史学理论探讨时的中心议题:既要识别电子游戏中蕴含的对编史学的颠覆性,又要将电子游戏的独特性置于更广泛的史学范式变革之中。另一篇早期经典是克劳迪奥·福古( Claudio Fogu)2009 年的《历史意识的数字化》。它将电子游戏的特质与可能性,放在“历史意识”的变迁这个更为宏大的叙事之中,认为:一方面,电子游戏并非孤立现象,它和超文本、对影音材料的数字再媒介化等发展一样,都在挑战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而将历史空间化;另一方面,电子游戏又与其他媒介技术不同,其中的交互与选择,使得它不是在描绘过去的“事实”,而是让玩家沉浸在模拟之中。这意味着,如果电子游戏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要形式,那么历史将不仅关乎过去的实然,也成为可能性的领域——而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诗学、哲学、历史学关系都将变更与颠覆。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历史游戏研究的深入,它也从早期“宣言”式的元历史/ 历史哲学构想,落实于更丰富、多层面,也更温和的细节讨论。 电子游戏的媒介特性如何影响它对历史主题、历史叙事的呈现,依然是最核心的议题。但是学者们很少再抽象宣告——在电子游戏之后,历史将关乎可能性,关乎“本应如此”或“也可能如何”;也不再以策略游戏作为最典型的电子游戏,以“模拟”作为电子游戏的最突出特征,而关注更多的游戏实例,游戏本体论上更多元的可能性。相应的,电子游戏如何“再现过去”也被视为值得关注的问题,而不再被视为错误的提问方式。
比如 2013 年马修·卡普尔( Matthew Kappell) 和安德鲁·埃利奥特( Andrew Elliott) 主编的《游玩过去:数字游戏与历史模拟》( Playing with the Past: Digital Games and the Simulation of History),作为摸索历史游戏研究领域边界、架构的早期经典,明确表示自己以游戏如何“再现”历史、“再现”过去作为主题,为“流行文化如何描绘历史”这一更传统的研究课题提供了新视角。比起元史学或历史哲学问题,它更倾向于分析具体游戏案例中的叙事机制与倾向,比如其中的进步观念、西方胜利主义、英雄史观、性别偏见,等等。2016 年,亚当·查普曼( Adam Chapman) 在《电子游戏作为历史:电子游戏如何再现过去、为历史实践提供机遇》( Digital Games as History: How Videogames Represent the Past and Offer Access to Historical Practice) 中,对何谓历史游戏研究、如何做历史游戏研究进行系统架构,尝试为历史游戏研究的边界、路径、分析框架设定规范。它将历史游戏纳入通俗史( popular history) 的框架之中,将历史游戏研究的重心放在了电子游戏作为历史再现上,并从其他通俗史比如电影历史研究中汲取理论与实践。
除了专著与论文集,期刊组织的历史游戏研究特刊同样呈现出对“再现“问题的关注。2016 年,《 重思历史:理论与实践》( Rethinking History. The Journ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组织了最早的历史游戏研究专题,亚当· 查普曼等学者在导言中,直接将历史游戏研究界定为“对那些以某种方式再现过去,或与对过去的话语相关游戏的研究”。专题中的论文,也更具体地讨论游戏如何处理反霸权的历史话语与政治记忆,历史事件的流行记忆、反事实幻想与历史反思如何在一款游戏中融合 ,不同群体如何从同一款游戏中经验和建构不同的历史内容。2022 年,《历史与理论》( History and Theory) 的“数字历史与理论”特刊中,对历史游戏研究著作的书评同样将“游戏如何再现过去”,视为“数字如何改变历史学”大转型中最值得关注的内容。如前文所指出,在这一时期,随着越来越多学者的加入,围绕电子游戏展开的史学理论探索,从历史与过去、历史与真实等元问题,落实为更细节的编史学讨论,比如电子游戏倾向于沿用怎样的、哪个群体的史观。历史研究学者们固然重视电子游戏的媒介特性,但已经不再执着于以电子游戏做“模拟”而非“再现”这一论断,并将它与影视等大众媒介区分开来的立场。相反,学者们更倾向于将其他大众媒介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迁移到电子游戏分析之中,在流行文化研究和大众媒介研究的羽翼下展开工作,尤其是加入到接受研究工作中,讨论学院外的历史诠释与记忆问题。
电子游戏研究确与其他大众媒介有着极大不同,甚至蕴含颠覆性变革的可能性。历史游戏研究始于对这些差异与变革的意识,并随着研究深入,日益关注对已有史学工作和传统的承继,将自己视为这些既有趋势的推进,而不是全然外来、割裂的工作领域。和数字史学的发展一样,历史游戏研究的兴起,始于从数字媒介技术中看到历史“书写”方式的变革;也和数字史学一样,随着工作的深入,逐渐展现与看重融入其他史学领域、与其他史学学者对话、处理更传统的议题的能力,以此融入整个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型之中。

《十字军之王 Ⅲ》
历史游戏研究从期的宣言、倡议、历史哲学思考、领域规范建构,逐渐融入史学研究工作的日常,落实到对具体材料的具体分析。学者们常常会回到自己的受训领域与原工作领域,或与其他的研究潮流、动态关联。历史游戏研究并非在真空中横空出世,它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数字史学、公共史学与通俗史研究、媒介研究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研究视野与方法。
比如,对公众及其历史实践的关怀,意味着即使是学院史家的作品,也只是另一种历史诠释,而非绝对事实和真理,人们也总是投身于西西弗斯般的对“过去”的诠释与再诠释中。对于媒介技术尤其是数字媒介技术影响力的认识,使得学者们意识到 21 世纪历史教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理解“过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媒介化、再现与接受。“过去”总被也总需要被不断重述与再诠释,尤其需要以当代人能理解、愿意接受的媒介形式表达出来。因为“过去”虽然“在那儿”,但是它需要一代代人的关注与传递,才能跨越漫长的时空——这便是历史游戏研究者转向接受研究的学理基础。
或许越是研究更遥远时空的历史学家,越是深谙这一点。毫不奇怪,古典学与中世纪研究领域的学者最投身其中,以论文集中的一个版块,乃至于一整本论文集或专著来讨论游戏如何“接受”他们的研究时段。在2007 年,古典学接受研究网络( Classical Reception Studies Network) 就支持召集会议,讨论古代世界如何成为大众文化的灵感,并重点关注电子游戏如何“接受“古典世界。其主编邓斯坦·洛( Dunstan Lowe) 指出:接受史的视角,有助于勾连电子游戏与其他媒介,将电子游戏中的历史再现置于大众媒介的历史再现的承继关系和关系网络之中。这一方面将电子游戏置于更厚重悠久的媒介化与再媒介化传统中,识别其中的通俗史知识,另一方面也能探索电子游戏中的形象或叙事与其他媒介中的有何不同,这种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源于电子游戏的媒介独特性,尤其是玩家需求、挪用与再创造。
中世纪研究也迅速跟进,2014 年丹尼尔·克兰( Daniel Kline) 主编的《数字游戏重新想象中世纪》( Digital GamingRe-imaginesthe Middle Ages) 探讨“真实”的中世纪元素故事与神话,关于中世纪的传说迷思及其变体和融合,当代关怀、投射、偏见乃至于误解如何在电子游戏中融合。它呼吁历史游戏研究关注“前史”,也就是桌面游戏、影视、小说等艺术和文娱形式中相关的历史主题如何变形与延续,进而进入电子游戏之中。经此拓展,对电子游戏的接受研究,既要分析电子游戏如何跟进学院中的新进展,又要跟踪它如何回应玩家所熟悉的通俗史。
近代早期研究大概在同期加入讨论,比如 2014 年托拜厄斯·温纳灵( Tobias Winnerling) 和弗洛里安·克施鲍默( Florian Kerschbaumer) 主编的《近代早期与电子游戏》( Early Modernity and Video Games) 认为,电子游戏等大众媒介中的叙事与想象,深陷于当下,以至于游戏中的历史实则只是现代性本身的故事,其中“只有一个 ‘ 时代’,也就是现代本身”。这意味着电子游戏中的历史信息,更多的是在体现过去对于我们的意义、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如何被一遍遍再述或者说再玩。
从接受研究的角度做历史游戏研究,表明学者们尝试将历史游戏研究融入已有的研究工作与传统之中;或反过来挖掘它对于更“主流”的历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首先,对古典学研究这样看似备受尊崇、被追溯为本源,但是也经常被认为欠缺与现实关联以及实际效应的学科领域而言,与新的数字媒介相接,关乎学科的 “生存”大计。其次,历史游戏研究也是历史学家增强自己对公众和公共事务敏感度的重要探索。在数字时代的数字鸿沟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电子游戏研究探索主要由身为“数字原住民”的年轻一代承担,因此,它既是历史学处理与时代、与其他学科关系的探索,也是它处理自身代际问题的重要工作。最后,围绕电子游戏展开接受研究,不只是为了让历史学在新时代存留、发展的一种权宜之计,它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它探讨关于过去的知识在跨越时空时,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又在哪些地方有着高度的稳定性。这本身也是位于史学核心的研究问题。总而言之,历史游戏研究探索数字时代的学科存亡、学科责任,以及传统议题的承继与延续,这些也都是数字史学的中心工作。

《中世纪王朝》
从电子游戏最初进入历史课堂开始,教研人员便从实践经验中意识到,当玩家群体、游戏文化、游玩目标与教师引导等因素存在差异时,人们从同一款游戏中获得体验与信息截然不同,因此,历史学者从游戏中解读出的内容,与电子游戏的真正影响或许差异甚远。然而时至今日,围绕着电子游戏生产与游玩展开的系统性经验研究依然非常不足,这种欠缺也被视为历史游戏研究最为严峻的问题之一。
最关注电子游戏问题的历史教学探索,希望能做出行之有效的课堂设计,再结合评估推广经验,因此非常重视玩家在课堂中与课堂外实实在在的游玩经验。比如 2012 年,克莱德( Jerremie Clyde) 和威尔金森( Glenn R. Wilkinson) 在讨论游戏模组的教学应用时指出,玩家群体的差异、不同社会文化和背景,会带来非常不同的游戏体验与“收获”。游戏能传递怎样的史实和编史学观念,不完全取决于游戏本身,取决于它在什么背景下、怎样的知识和文化网络中、如何被玩。然而,越来越多的历史游戏研究工作,其研究者首先以学者而非教师的身份介入,使之往往未能继承期教学研究中的这些经验面向,未能意识到真正让游戏成为游戏的,是玩家的游玩。历史学家固然可以研究游戏的文本、音乐、声音,以及它对其他艺术或文娱产品要素的挪用,但脱离玩家视角,这些分析则不够切题。
此外,对电子游戏的接受研究,虽然理论上要求从电子游戏的媒介特性出发,并关注电子游戏在学者审视目光之外的切实遭遇和影响,但是直到21世纪20年代结束,这种设想依然缺乏成功的实践范例。比如 2020年,罗林·杰克里斯蒂安( Rollinger Christian) 指出,至今几乎没有对经由电子游戏的历史知识接受过程的经验研究,这已经成为明显的方法论短板。同年,亚当·查普曼在反思历史游戏研究究竟何去何从时也认为,即使学者们在理论上知道,游戏中的讯息并非固定内容,接受者不是固定不变的被动群体,现有的研究对玩家实践与视角依然所知甚少。查普曼还提出,经验研究的关注对象也应拓展,涉及电子游戏从生产到消费、到接受与延伸的全链条,将游戏企业的利益相关人、制作人与历史顾问、游戏模组制作者和其他二创创作者、消费者的实践活动都纳入考察对象。
这些意识和呼吁并不容易迅速实现。一方面,历史学家的“技艺”,有其边界与短板。比如杰克里斯蒂安提出的对成百上千人进行调查问卷以及访谈,本就是受训于本文解读的历史学者们不那么熟悉或擅长的领域。另一方面,学院中的历史学家,有着对自己责任与权威的坚持。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将自己视为历史知识的守门人,他们围绕电子游戏中的历史信息是否“精确”与“真实”进行价值评判,是因为游戏文化中的确存在着诸多“有毒”之处,需要获得警示或纠偏———即使他们同时深知“是否精确、真实”本身不是那么合适的提问方式,也同样深刻反思“书面学院历史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的合理性。
历史游戏研究对于经验层面的关注,展现了学者们探索如何从游戏的制作方、玩家和二创群体中,看到更多元的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主体,更真实的历史诠释过程;反思以学院史家著作与传统为标准的传统评价模式,是否已经不再适用于这个时代。更重要的是,历史游戏研究者将电子游戏放回它原本的社会背景之中,置于人们日常的使用、创作和再创作中,以此来理解数字技术对大众的历史信息获取与表述、对社会历史意识的真实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游戏研究所关注的电子游戏,不只是学院氛围下、学者眼中的新媒介,而是正切实发挥着影响、改变大众历史意识的新力量;历史游戏研究不再局限于电子游戏本身,而是以它为重要结点的数字技术网络,以玩家为重要身份的新世代;更重要的,它看到了电子游戏等数字媒介受众的主体性,认识到数字技术的真正影响,可能超出学界的分析,甚至超出它的设计初衷。而数字史学工作中,最困难而重要的方面,正是理解数字媒介的用户如何不同于传统纸质媒介的用户,他们的“参与”如何构成了数字媒介的本质,又如何对学者们的教学、研究、基础设施搭建,对历史学整体上的数字转向提出挑战。
通过梳理历史游戏研究的演进我们看到,历史教师们率先投入工作,不仅因为电子游戏是最容易接近学生群体的方式,更因为他们关注何谓数字时代的历史素养、数字时代历史学家的技艺——电子游戏作为当代青少年获取历史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它提供了新的“阅读”与“书写”历史的方式,解读与使用电子游戏是重要的历史素养。类似的,当历史学家对电子游戏进行史学理论探讨时,他们并没有将目光局限于电子游戏本身,而是以电子游戏作为数字媒介的代表和典型,以此为切入点思考历史学正经历的数字化转型与媒介变革。不仅如此,随着自身的推进,历史游戏研究寻求与已有的领域和路径融合,立足于已发生、正在进行中的史学趋势。它看到的是整个历史学领域的可能性,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新研究领域。最后,在对玩家经验,也就是数字技术使用者经验的关注中,它并没有将史学的媒介变革视为史家的自留地,而将更广泛的公众也纳入其中。由此,在整个历史游戏研究的推进过程中,关注的是数字时代的历史学习、研究与交流这个更为宏大的问题,在公众—媒介关怀上与数字史学一脉相承。
3
历史游戏研究的共识与启示
如果以标杆性学术刊物的公开发表作为依据,电子游戏正日益被历史学“承认“为学术研究对象,则 2021年是一个标志性节点:《美国历史评论》(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在其2021 年的春季刊上,第一次刊载了以电子游戏为主题的文章,并在传统的书评版块之外增添了游戏评论版块,对《刺客信条》( Assassin’s Creed) 系列中的三部作品进行评议。考虑到电子游戏因其“参与性“,让玩家与设计师、历史学家分享权威,被认为天然就是某种公共史学形式,而历史学研究者至今也主要在公共史学的语境和框架下讨论电子游戏 , 2021 年,重要公共史学刊物《公众史学家》初次刊载电子游戏研究论文,讨论电子游戏与历史教育、历史学习的关系。这些“顶刊”的关注也并非 2021 年的昙花一现,2022 年与 2023 年,《美国历史评论》又分别刊载了关于历史游戏研究的书评,以及历史游戏的教学应用文章 。类似的,《公众史学家》也于 2024 年继续分享如何以电子游戏做公共史学工作,历史学家如何成为历史游戏开发者等探索。
 《刺客信条》
《刺客信条》
上述过程表明,历史游戏研究逐渐被更为“主流“的历史研究者看到。这一变化的基础在于,历史游戏研究已经在这片学术蓝海中做出了不少开拓,学者们的研究不再是零星的孤岛,而形成了更多的对话与共识,这些探索甚至能够反过来为更出现、更为成熟的史学工作,比如数字史学提供视角。
3.1 历史游戏研究的路径方法
历史游戏研究最常采用、最基础的研究方法,便是评议游戏内容之历史“精确性”( accuracy) 与“真实性”( authenticity)。也就是历史学者基于各自的受训领域和工作领域,以学界共识以及最新进展为标准,对比电子游戏中的历史再现,对其是否足够“精确”与“真实”进行评议。毕竟,以当代史为研究领域的学者,或有能力直接推进“当代社会与文化中的电子游戏史”等研究工作,其他受训于古典学、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的学者们,若要投身电子游戏研究,最熟悉的依然是自己的研究时段、地域、国别,至多能经由本领域的学术史和接受史,触及当代世界。因此,电子游戏中的历史细节、历史叙事与解释是否符合学界理解,符合哪个时代的学界理解,是他们最容易在历史学找到专业基础,进而展开工作的路径方向。
不过,考察电子游戏历史内容的“精确性”和“真实性”也是最受到批评与修正的研究路径。首先,它将学院史学树立为最高权威与标准,而这种姿态正是关注电子游戏的历史学者一开始就尝试对抗的境况。其次,“精确性”“真实性”是难以清晰界定的术语,历史游戏与学院历史的“符合度”研究,也远不是一种客观的比较。在大的共识之外,选择哪些、哪派学者的观点作为标准,抓取游戏中的哪些内容加以考察,都要由研究者来做出选择。再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研究者往往对电子游戏有着不恰当的期待,进而谴责电子游戏简化历史、片面呈现历史,或是未能跟上研究进展。但这些问题,同样可能存在于更“严肃”的学院历史作品与教科书之中。最后,单纯评判“精确性”“真实性”意义不大,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提问方式。无论电子游戏中的历史讯息是“正”是“误”,它们均产生并流行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之中,玩家以特定方式、在特定社群中接受它们,玩家认知由此常常不同于少数历史学者的解读与观感。更重要的地方在于,游戏要给玩家选择与互动的空间,就必然包含某些“反事实”的设置或走向,对于精确性和真实性的要求忽视了游戏机制与媒介特性。
在接受研究和记忆研究中,“跨媒介”与“再媒介化”是重要的考察方向。它们首先意味着将电子游戏视为新的媒介技术,认为其技术特征至少与游戏的历史内容同等重要:游戏的历史背景与叙事,要经由游戏机制设计、通过玩家参与和互动,方能成为玩家的经验、认识与记忆。其次,“再媒介化”意味着在更广泛的流行文化史中考察电子游戏中的历史细节、叙事与史观,尤其是电子游戏如何承继小说、电影、电视剧中的已有内容,并对它们进行再创造,共同参与公众集体记忆的建构。“跨媒介”意味着关注玩家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也就是玩家在自组织与参与性文化之下,主动搜寻相关资料、寻求社群支持与交流讨论、对电子游戏进行补充、修正和再创作,即将玩家活动也纳入历史游戏研究的考察对象。
经由对游戏主题、内容“跨媒介”与“再媒介”历程的追溯,历史游戏研究者们看到,电子游戏中的历史绝不是对最新学术进展的单纯简化、通俗化或是扭曲。相反,它往往离流行文化所塑造的公众记忆和想象更近,延续早年的流行小说、电视剧、电影中的主题与叙事,或是在历史或架空历史中影射当代问题、呼应当代焦虑。玩家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在当代大众文化的背景中,带着更多的“伪知识”和刻板印象,怀抱当代的政治议程、社会态度、意识形态关怀,而接触游戏。因此,电子游戏更接近于一个观念与记忆的竞技场,学术进展、更传统( 陈旧) 的历史知识、流行文化中的历史记忆、当代议题投射、创作者理念、玩家背景与主动性,统统在此交汇。历史游戏研究也由此与玩家研究,与更广泛的大众文化研究交融,对这个“竞技场”进行条分缕析。
从对“精确性”与“真实性”的评判,到接受研究与记忆研究,历史游戏的路径方法对于数字史学有着怎样的启示?我们在回顾数字史学的路径方法时看到,数字史学独立于计量史学,从第二次“历史与计算机应用”的浪潮中诞生,主要以互联网、数字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为触动因素,以公共史学承诺为基础。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受限于发表体系等学术体制,人们更熟悉其量化分析等侧面,而很难经由论文和专著,看到数字史学中那些基于数字媒介、以学院外的群体为受众的工作,而历史游戏研究恰恰能对如何评判、理解、推进这些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历史游戏研究提供了媒介分析的视角:不同媒介形式,倾向于或适用于再现不同的历史真实。数字史学在以数字技术为“工具”时,也需意识到这些“工具”并非中性,其特征与倾向,会影响到学者们借助它们所能处理的议题、表达的内容、触及的受众。在借用那些以交互性、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数字技术时,更需要将使用者与受众的经验和自主性纳入考量之中。这些对媒介的敏感,对公众自主性的关注,尤其是对用户生成内容技术的理解与使用,恰位于数字史学工作的核心,历史游戏研究则为其提供了抓手和案例。

历史游戏研究主要集中关注哪些主题与内容?在研究问题与初步结论上,有哪些对话空间、达成了怎样的共识?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关注与分析的历史游戏,已经涉及大部分历史时段。他们也从当下最受关注的编史学问题出发,对电子游戏中的历史精确性和真实性加以考察,形成了一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而最初也最激动人心的问题——电子游戏如何是一种新的历史形式、新数字媒介如何改变历史学科本身,则一直贯穿历史游戏研究发展始终,也是其展望发展方向的重要动力。我们接下来将围绕历史时段、编史学问题、游戏机制分析、电子游戏与历史学未来等主题,梳理历史游戏研究领域已有的共识。
就历史时段而言,以古典、中世纪、近代早期、工业化时期的美国及以一战为背景的电子游戏,都得到了专门研究。学者们也对哪些时段最受游戏生产商青睐进行了统计分析:以古代、中世纪、近代早期为时代背景的电子游戏数量均不足 10%;大部分的电子游戏,将历史时段定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或者说近代晚期,其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历史背景的游戏又尤其多。这种以二战、冷战以及中东战争作为主要历史背景( 或历史影射) 的做法,体现了电子游戏作为文化产品的特征:它的内容要有卖点,就要迎合乃至于激发恐慌,这些战争背景体现了西方国家对于切身威胁的大众认知。
随着领域发展与精细化,从一款或几款游戏入手,以小见大构成了研究常态。虽然以历史游戏研究领域目前的规模,还不足以支持更多围绕历史细节展开的学术对话,然而,学者们在历史游戏的编史学倾向上有了许多共识。他们重点关注电子游戏如何展现文明与野蛮、帝国、殖民、战争( 尤其是二战与冷战)、种族、性别、西方霸权与非西方国家的抵抗、美国“西部”与边疆等主题,并由此看到,电子游戏有着成为文化霸权工具的倾向与可能性。具体而言,电子游戏的历史叙事与历史理解,常以西方白种男性异性恋视角为中心,它们的史观,或者说对于历史发展趋势与逻辑的理解,有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西方胜利主义倾向,更是常常将美国置于发展的终极方向、人类文明的巅峰与模范。这种倾向与问题在模拟或策略类游戏中更为清晰可辨,它们常为更陈旧的辉格史观主宰,以现代西方对于何以成为它自身的理解为基础。因此,有学者指出,电子游戏很容易对当代议题进行过度投射,其中的历史缺乏“历史性”,只是现代性本身的故事。而警惕通俗史以当下吞噬过去的倾向,正是历史学维护自身边界与权威的原因所在。这也是虽然历史游戏研究立足公共史学传统,有着突出的反权威倾向,依然免不了对游戏中的历史细节与叙事方式展开价值评判。
3.2.4 电子游戏与历史学未来
历史游戏研究没有止步于分析游戏中的历史形象与信息,还有着更大的野心。从最初的理论思辨开始,它从电子游戏中看到的,便是对整个历史学科,甚至是大众普遍历史意识的数字化。这场变革之深远,可能不仅指向19世纪以来的兰克史学与历史的学科建制化,甚至指向古希腊以降的史学传统,以及它与其他人文艺术的关系。
几乎所有历史游戏研究的参与者都认同,某种关乎学科领域的变革即将或是正在发生,而电子游戏是跟进它的绝佳线索。但是,这种变革的具体形态是怎样的,如何发掘利用电子游戏最独特的技术优势,如何一点点践行变革,却至今是个谜题。有学者以电子游戏进行大规模模拟作为重要发展方向,认为它能够探索反事实在历史学中的位置,更直观展现个体选择在复杂系统中的影响,凸显历史偶然性的意义,探索历史决定论与偶然性的边界。也有学者从编史权威的去中心化、民主化出发, 探索“玩家—历史学家”( player-historian) 与“开发者—历史学家”( developer-historian) 的角色身份,不仅仅设想如何经由游戏让更多人参与到历史对话中,也设想通过游戏来做历史的可能性。历史学家如何通过参与游戏制作来做历史,也在逐渐形成实践范例。也有学者基于历史学家的技术与资源限制,进行了做游戏的经验分享。还有学者指出,电子游戏对于历史的最大启示或许在于“玩”( play),通过“玩”数字工具、以玩家方式与数字技术打交道,历史学家才能真正找到更有意义的使用数字技术的方式。又因为数字史学的困境恰好在于其与定量研究的高度绑定,仍需探索更具突破性的使用数字技术的新方式,以体现数字史学之不同于计量史学,“玩”构成了数字史学的突破口,而电子游戏所探索的虚拟世界构建与架空历史讨论则构成了更为具体的解决方案。由此,游戏历史研究的展望与数字史学的展望合流,共同指向了历史学本身面对数字技术和数字时代的根本变革。

4
结语
广义的数字史学,面对着世界的数字化转型,使用各种数字技术开展工作,进行学科领域的数字转向探索。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当下最重要的史学趋势之一,所有历史学家也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了数字史学之中。数字史学也面临着发展瓶颈。在刻板印象中,它很容易被误解与简化为量化研究;在整体上,它对于史学的数字化未来的承诺,亟需落实为具体的成果或范例。历史游戏研究,能为这两方面的困境的解决提供支持与出口。
我们现今的“数字史学”并非“计量史学”,而是以公共史学理想为基础,以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背景。对这一起源的遗忘或误解,正因它实际上在处理整个历史学科在数字时代何去何从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关乎历史遗产保存,关乎新的“阅读”方式、“书写”方式,也关乎学院与公众的关系。当数字史学囊括了在数字时代使用数字技术,生产、传播、保存历史知识的全过程时,它需要一些特色元素与记忆点。而在现有学术发表体系下,最容易经由发表和出版出现于学界视野中的,是基于数据挖掘和量化分析的研究。与之相较,其他形式的数字史学工作,甚至包括那些标志着数字史学兴起的网页或 CD-ROM 公共史学项目,都没有如此特色鲜明。
电子游戏则不同。它汇聚了数字史学在意的数字技术特质,比如非线性、交互性、参与性等。它的制作与传播方式,玩家在社群中的游玩方式,也使得它构成了讨论数字技术如何促进历史学开放、共享、合作、去中心化等议题的切入点。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当历史学家转而关注电子游戏,逐渐在“历史游戏研究”这个标签下工作时,他们的探索也有着鲜明的数字史学特征:理解与培养数字时代的史学素养,探讨数字媒介对历史研究、呈现和传播方式及对公众历史意识的变革,探索史学传统与即将来临的媒介变革间的承继与桥梁,最重要的是将公众的史学理解和活动纳入变革之中——这些历史游戏研究的中心议题与数字史学的公共—媒介关怀一脉相承。
电子游戏汇聚了公共史学关注的数字技术特征,它的流行程度与影响力使得它成为一窥数字媒介将如何改变历史工作方式的窗口,而历史游戏研究从始至终就着眼于媒介革命下的历史学这个更为宏大的数字史学主题。由此,历史游戏研究也可被视为数字史学工作的一个部分、一个延伸方向。不仅如此,历史游戏研究的路径方法、主题内容,比如融入传统史学工作之中、从其已有趋势出发寻找支持历史游戏研究/ 数字史学的内生动力,关注历史知识的传播环节以及受众的接受、再创造和记忆,分析数字技术天然的倾向及其在社会背景与市场逻辑下的倾向,关注用户切实使用与共建中的而非学院史家设想中的数字媒介,等等,也能为更广泛的数字史学工作提供启示。

校对:陈艺菁
排版:祝慧敏

特别说明:本文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权请后台联系小编删除。

